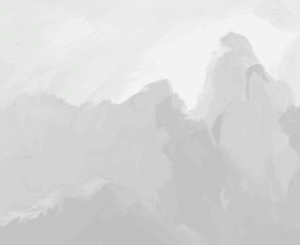1926 — 2002
吳維僔
為信仰、為維護基督徒的良心與尊嚴而寧死不屈,寧折不彎的基督徒傳道人;二十幾載的牢獄生涯,造就了這位名揚中外的“中國的以巴弗”。
吳維僔的外公名袁昶,晚清時期,曾在安徽蕪湖做道臺,因治水有功,深受當地百姓愛戴。後被調到北京,做了蕃臺,是個二品官,在朝中侍候,曾代表清廷與沙俄簽訂條約。1900年,義和團興起後,不幸被“拳民”殺害。其12歲女兒袁季蘭(吳維僔之母)隨母親逃往江蘇松江避難。亂定之後,朝廷將袁昶等三位忠臣葬於杭州西湖邊,稱“三忠祠”。
在松江,袁季蘭有機會進入美國衛理公會宣教士開辦的教會學校——慕衛女校讀書,從她們學習聖經,並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中學畢業後,19歲的袁季蘭嫁到浙江東陽的吳家大戶,其公爹吳品衍是清廷朝臣,與袁昶私交甚好。婚後三年,全家搬往杭州。吳維僔父母共養育八個孩子,五男三女。長子和次子早年不幸夭折,吳維僔排行第六。
吳維僔父親原在省政府里作科員,後來進入工廠工作。母親先在學校教書,後因看到為主傳道的人少,就辭去教職,帶著吃奶的小維僔到南京,入金陵女子神學院讀書。畢業後,被分派到松江衛理公會教會作傳道。
吳維僔於1926年4月生於江蘇松江,出生後,母親為他取了個聖經中的名字,叫以巴弗(歌羅西教會基督徒,為福音的緣故曾與保羅一同坐監),沒想到他一生的遭遇與這個名字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國的以巴弗”。
吳維僔從小在教會環境中長大,除在教會里上主日學外,家里還有禮拜聚會等,母親在信仰和生活上對他的影響很深。但上小學五年級時,他思想開始叛逆,甚至反對神有四、五年之久。直到1941年5月的一天,當他認真跪下來禱告時,神的靈光照他,使他看到自己的驕傲,真誠地向神悔改認罪,從而經歷了重生。從那時起,他里面就有了主耶穌基督的生命,內心充滿了平安和喜樂。
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許多教會學校受戰事影響而停辦。1942年,吳維僔考入浙江省立浙西三中。自從重生之後,他在行事為人上,盡可能遵從聖經真理而行,寧肯吃虧,也堅持不說謊、不討好別人,不拜偶像(包括向領袖像行禮);在生活中嚴格要求自己,對付自己的脾氣和不好的習慣,並刻意鍛煉自己節儉、受苦的心志。在浙西高中的三年里,學習生活雖然緊張,但他一直認真讀經、靈修,在靈性上有很大長進。
讀完高中後,吳維僔先在浙西一所農村小學教書,半年後回到其松江母校慕衛教會小學任教。1946年,在上海中華神學院所舉辦的傳道人退修會中,內心大受感動,遂決志奉獻自己,於同年九月入讀中華神學院。就讀期間,在上海守真堂實習。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吳維僔到守真中學擔任物理課教師;1955年調入上海同濟中學教高中物理。就教會生活而言,吳維僔曾一度離開守真堂,參加南陽路聚會處的聚會與敬拜,並擔任一個組的負責弟兄。1951年8月,他又回到守真堂,並擔任執事。1955年8月,因拒絕加入“三自愛國運動”,拒絕批判王明道,吳維僔再次被迫離開守真堂。
1956年,經人介紹,吳維僔與天津的一位基督徒女教師相識,次年二人在北京結婚,由徐弘道牧師為他們證婚。在此期間,吳維僔曾去拜訪第一次被捕獲釋,時在極度痛苦中的王明道。交談中,吳期待王明道“能像聖經中的參孫那樣,待頭髪長出後,再打那制勝的一仗”(見《中國的以巴弗》,148頁)。這是吳與王唯一的一次會面。婚後,吳氏夫婦定居於天津。為生活在一起,吳維僔於1957年7月從上海調到天津,在四十六中學教物理。
因當時天津僅存的四間教會都在“三自”組織的控制之下,吳維僔就和妻子在家里自己禱告、聚會敬拜神。因其在學校中仍堅持基督教信仰,在政治學習中表現不熱心,於1957年12月被下放到天津北郊劉安莊從事農業勞動。期間,他仍然堅持讀經和禱告的習慣,若有農民問起他關於基督教信仰問題,他就借機向他們傳福音、作見證,並將此視為向神、向人當盡的本分。為此他也常被領導斥為“散布宗教迷信”,受到不少責難。當時下放勞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造人的思想,但他因堅持基督教信仰,就總過不了思想改造這一關。眼見別人都一批批地抽調回城里,但他卻一次次被留在艱苦的農村,繼續接受思想改造。
1959年12月,吳維僔被調往天津東北郊的一個棉毛加工廠工作。因其一如既往,繼續讀經、傳福音和作見證,受到許多刁難,常常被派去干最髒、最累的活。有一次為了能把他與別人隔開,領導竟分派他去放羊達半年之久。不想這反倒為他提供了很好的學習聖經的機會。半年時間里,他詳細查考聖經,並做了許多筆記。
1961年底,吳維僔被調回天津,在無線電儀表中專學校(原四十六中)工作,但不是作教師,而是擔任校俱樂部管理員。半年後,又被安排在物理實驗室作實驗員。在此期間,他與北京、上海等地的主內弟兄姊妹的交往日多,並編寫、復寫《主內交通》文字資料寄往各地。此舉當時被看為“非法罪行”或“反革命活動”,他也預感到不久自己可能要為此遭受逼迫與患難,於是開始定期禁食禱告,為將要來到試煉作準備。
1964年7月30日,吳維僔被公安局傳訊、抄家。因在審訊中拒不開口而被收押入看守所。此後在一個月內一連八次被提審,但皆“拒絕交代案情”。此後,不管監獄當局如何軟硬兼施,他都抱定“不交代、不認罪、不悔改,只一心仰望、交托給主”(同上,219頁)。在看守所關押期間,由於他堅持“飯前謝恩”和定期禁食,飽受餓飯、灌食、毒打、重銬和批鬥等種種折磨,吃盡了苦頭,但他終未屈服。1967年2月,吳維僔被控以“反革命罪”,並且因“在監內不思悔改,頑固不化,對抗無產階級專政,反動氣焰極為囂張”,而被判為無期徒刑。但他效法主耶穌,不申冤,不上訴,甘心忍受,將此視為為主受苦,背十字架。
判決後,吳維僔在天津監獄里的勞改隊服刑。自他被捕直到判刑,他的妻子作為“反革命家屬”,在監外也受盡了苦難和折磨,最後在巨大壓力下,不得不與吳維僔離婚,而改嫁他人。他的三哥也因為是個基督徒,而被打成“反革命”;母親在“文革”中也飽受紅衛兵的摧殘,以致說話不清。最後,全家人——父母、三兄三嫂和子女,都被遣送回祖籍浙江東陽農村,不久,父母先後離世。此後,吳維僔再無后顧之憂,在獄中立志“聽主的話,遵行神的旨意,在任何事上都要把主放在第一位,作好一個基督徒所該有的見證。”(同上,264頁)
1967年4月,吳維僔被轉押到寧夏平羅“瑪鋼廠”勞改隊勞動改造。文革時期,因其堅持不讀毛語錄,不唱革命歌曲,不高喊“萬歲”,不向毛像敬禮,以及仍然堅持飯前謝恩等,被視為“反改造份子”,多次遭受毒打和各種非人的折磨,經歷了九死一生。
1979年2月,吳維僔又被轉到寧夏銀川的風機廠勞動。此時,監獄大墻外的政治氣候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許多犯人通過寫檢查、認罪或申訴等以獲得減刑或釋放。但吳維僔仍如起初一樣,為維護一個基督徒在神面前的聖潔和良心,堅決不悔改、不認罪,也不申訴或叫屈。他堅信主耶穌的話:“不要為自己申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同上,298頁)
雖然吳維僔一直堅持到底,“死不悔改”,但到了1981年春季,寧夏高等法院還是為他減刑為六年。但當減刑裁定書送到他手中後,看到其中有句話說他“確實悔改”,他卻認為這是弄虛作假,是對自己的侮辱,因為他從來沒有為甚麼所謂的“罪”悔改過。他不愿違背自己的良心,更不愿以謊言來換取減刑或自由,他寧愿將苦杯喝盡最後一口。於是他寫信告知法院,說自己从未悔改認罪过,是法院裁定错了,並将裁定書寄還給法院。
他寫道:“作為一個基督徒……,所應該著重考慮的、尋求的、分辨的,只是我們所說、所做、所想,是不是聽主的話,是否符合聖經真理,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是否蒙主的悅納。若是,則即使掌權者定罪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就讓他定罪吧。他即使定罪,我們仍當如此行,絕不能因怕他們定罪,就不如此行。他們定罪,只是暴露出他們與基督為敵、悖逆神的本質而已。主耶穌自己也曾為遵行神的旨意,實踐神的差遣,取悅於神,而被人定為背叛該撒、自立為王、誘惑國民等政治性質的重大罪名,主耶穌絲毫不為此爭辯,而是專心順服,按父的意思釘十字架,喝盡了父所賜他的杯。我也應該學主的榜樣,面對人所定我的這些政治性罪名,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根本不去考慮這些,只一心遵行神的旨意,喝完神所賜給我的杯。” 為著這緣故,吳維僔拒絕這種“骯髒的自由”。
自1964年入獄始,直到1980年春,他有十六年之久與外界隔絕,不被準許與任何親友通信,故外面的人也不知他是死是活。八十年代初,時局緩和後,吳維僔的已獲平反身住福建泉州的三哥四處寫信,尋找他的下落,方知他在寧夏銀川風機廠勞改。1980年3月,三哥千里迢迢趕到監獄探視吳維僔,在監獄當局的監視下,會面交談半小時。此後,吳維僔得以與外界通信,和主內的弟兄姊妹也恢復了交通。
當時,犯人的來往信件都要經過獄方的嚴格檢查。1982年,上海的一位弟兄寄給吳維僔一本中文聖經,即被獄方沒收。那時,他已經有十八年沒讀到聖經了。1983年,他大姐試著寄給他一本英文欽定本聖經,監管隊長一看是英文書,就給了他。他如獲至寶,每日早起到教室里如饑似渴地閱讀。此後,環境愈加寬松,1984年,他又收到大姐寄給他的中文串珠版聖經,同時他與監外主內弟兄姊妹的來往信件也愈加頻繁,這些信件後來被整理成書,稱《主內交通》。
中國改革開放後,吳維僔在獄中的生活也有改善。1982年,監獄內辦起了文化學習班,吳維僔被指派為犯人們教授初中數學。由於這是他的本行,在教學上他更是盡心竭力,獲得監獄領導和犯人們的好評。吳維僔在獄中的最後五年,都是在獄校任教。無論他同意還是不同意,法院最後還是把減刑為六年的裁定“強加”(吳語)給他,刑期一滿,監獄方面就強行執法,趕他出獄。雖然他認為法院的做法是“骯髒的”、“可憎的”,但他為“順服在上掌權者”的緣故,只好“不得已而出監”。雖如此,他仍自覺以一個“獄墻外的犯人”繼續抗爭下去,以示:“我拒不接受你們的裁定,我仍然是一個死不悔改的無期犯人。” 並且從釋放之日起,他開始定期禁食,每周只於周一和周四兩天吃飯,以抗議法院對他的“弄虛作假”。
1987年5月28日,61歲的吳維僔正式出監。因著他的堅持,當局決定把他“養起來”,即在監外給他一間房居住,戶口落在風機廠,每月45元生活費。十多年里,他自覺過“墻外無期犯人”的生活,從沒離開過銀川或風機廠一步。每日他主要做的,就是接待各地來訪的主內弟兄姊妹,通過文字和各地弟兄姊妹交通,寫印《主內交通》,寄往各地有需要的人。他也常為別人購買聖經和屬靈書籍等。
吳維僔過著聖徒般的生活,他的日常生活極為簡單,睡在只是幾片木板拼在一起的簡陋床上,別人想幫他換一張床,他婉言謝絕。除了極低的生活開銷外,他平日最大的開銷就是郵資和影印費。因為前往探望他的弟兄姊妹太多,為了給訪客提供方便,他干脆自建了一個廁所。
吳維僔十幾年如一日,仍然堅持定期禁食的生活,直到去世都是如此。奇妙的是,他過去在監獄中所患的痔瘡、關節炎、痢疾以及咳嗽等疾病,全都不治而愈,而且所有老年病都不曾染上,睡得也非常好,堪稱神跡,他認為這些是神的特別恩典。
因吳維僔經常寫信給各地信徒,交流信仰上的各種問題,其中難免有些對“三自”教會的批評;也隨著他的影響日廣,所以從1996年開始,他多次被抄家和傳訊。1996年11月12日晚,他自出獄後第一次被抄家、傳訊。他被帶到公安局,在一大堆被抄的屬靈書籍面前,公安人員連夜審訊他。面對審訊,他一如既往,除了“無可奉告”四個字外,甚麼話都不說。公安局拿他沒辦法,只好放他回家。在吳維僔寫給他在臺北的四哥吳維健的信中說:“2000年6月,我被市公安局政治科第四次抄家後,今年4月23日再次來我住處進行第五次抄家沒收,不但《主內交通》等各文,且包括一切聖經、工具書、屬靈書籍在內的所有書籍洗劫一空”(同上,362頁)。面對淫威,他一直本著“不攔阻、不爭辯,也不請求”的原則。
在這種兇險的環境中,吳維僔於1999年12月,73歲時,寫完了自傳《中國的以巴弗》。在其“末了的話”中,他寫道:“主引領我作了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基督徒見證,打好不同階段中的屬靈爭戰。我自己毫無一樣東西可以拿出來夸口,因為沒有一個見證、沒有一次爭戰,是憑我自己能作好、能打勝的,都是依靠主豐滿的恩典,智慧的大能,才能作好,才能打勝。所以,一切榮耀都要歸給父神和主耶穌基督,他是唯一可稱頌的,唯一可信賴的,一切恩典、力量、智慧和一切祝福,都是從他而來。”(同上,358頁)
“求主憐憫保守我,施恩拯救我到底,能儆醒等候走好尚未走完的每一步,不致辜負主已為我舍身流血的大恩典,得以最終見到主的榮臉。”(同上,359頁)
2002年12月21日上午,吳維僔走完了他一生的十架苦路,在其簡陋的住所中安然離世,回到他所忠心、所愛、所事奉的救主耶穌那里去。在世享年76歲。
資料來源
- 吳維僔著,《中國的以巴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關於作者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