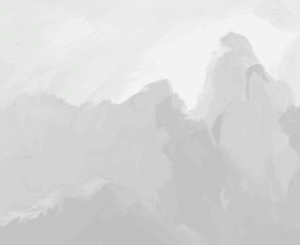丁惟柔于 1914 年 出生在北京什锦花园胡同的大宅院里,父亲丁锦因为曾经在上海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修习过日文,在友人的推荐下进入了袁世凯所辖的北京陆军部做翻译工作,却因此一脚跨入军队,从此打开日后权高位重的大门。她的母亲则因家境富裕,父亲又非常开明,让孩子很早就受西式教育,后毕业于苏州景海女中。她不仅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还会拉丁文与希腊文,在当时的中国真可谓凤毛麟角。
丁父在北京任职时,由于参与对日的情报工作,尽管当时对工作内容并不十分清楚,却因缘际会地与靳云鹏、卫兴武、魏海楼成为莫逆之交。日后靳云鹏曾担任国务总理, 其它两位也是北洋军政府皖系的大将,颇受陆军部重用。丁母因其流利的英文,曾经做过清宫福晋的英文老师。1921年陆军部成立航空署,在对外购买飞机时,需要有一位能用英文应付对外事务的负责人。丁父因着妻子的缘故,在宦途上更上一层楼,成为第一任的航空署署长。后因段祺瑞要求丁父派军机攻击孙传芳和吴佩孚时,丁父以军机只能轰炸外国人,而不能炸自己人而拒绝听命,从而辞去官职。
丁父辞官后,在朋友的建议下开了一家“正阳银号”,经营得法,使得丁家在钱财上一无所缺,维持着优渥的生活。在这样氛围中长大的丁惟柔,有着当时女子少有的开阔的见识与坚毅的心志。由于丁父出身于书香门第,对于子女的教育自然相当重视。虽然他宦途顺遂,但他坚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样的观念也成为丁惟柔一生的信念,帮助她度过许多难关;但也同样成为她性格上的一个阻碍,有着极强的自我意识。丁惟柔在她父母的身上看到了风骨、爱心、宽容,在在都对她日后的处世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
丁家的孩子就在这样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下出生长大,尽管宅院之外时局动荡,在高墙之内自有一份宁静安适,日子过得平静安稳,生活也不免奢华。但丁惟柔却是其中的异类,她只要一碗面,或吃个麻酱烧饼就觉得很满足。因为家里的孩子中只有丁惟柔一个不爱往外跑,常待在家里,所以丁母在管理家中大小事务时总带着她。耳濡目染之下,丁惟柔也学得了一些管家的技巧。
由于父母受惠于西式教育,丁家孩子当然也进入新式学校接受教育。丁惟柔读过一年的幼儿园。读完小学之后,又进入师大女附中,课业要求十分严格,她样样都以高分作为目标,尽力达到自定的标准。高中时,丁惟柔离家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正当此时,丁母病重,大姊耐不住性子在家照顾,她就毅然离开学校,天天陪伴母亲。可惜丁母病况仍不见改善,而于1932年4月辞世。此后,当家的权力与责任自然就转到了这位“二小姐”身上,一个仅仅十来岁的女孩就当了家,管理着一家上上下下二十几口人的生活,其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在此时画下了句点。
丁母虽然一生顺遂,但是一直以未能习医引以为憾,丁惟柔其实对医科并无多大兴趣,可是为着完成丁母的心愿,就以习医为第一志愿,考取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然而校方认为她体重过轻,质疑她的体力是否能够负荷沉重的课业,遂与她立下一个条件:若不能在半年内增加十磅就必须转至它系。但不管丁惟柔如何保养自己,体重总不见上升,半年后不得已只好转入物理系。其实她对物理就很有兴趣,因其本性就极为理智,所以分外着迷于井然有序的物理世界。也因习得物理专业,在日后生计遭逢困难时,即以教授物理为生,使她深深体会到万贯家产不如一技在身。
大学期间,许多女孩开始寻求未来的对象,丁惟柔也不例外,但她有自己的择偶标准,诸如不能小气、要有学问、为人正直清廉等都在其中。对于交往的对象都要审视一遍,如果不符就不继续交往。此时她认识了华东煤矿的朱家二少,不仅家财万贯,又有大方的气度,颇符合丁惟柔的条件,因此两人持续交往。可惜因着中日战争的爆发,两家失去了联系,婚事也因此耽搁下来。由于丁父是政府的高级参谋,丁家随着政府与学校的撤退到了四川成都。在那里,丁惟柔于1940年完成了大学课业,进入重庆的嘉华水泥公司担任经理之职。在这段时间里,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丁世祺先生。
丁世祺毕业于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后赴美国宾州大学进修,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在当时驻美大使胡适之手下任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回到中国大后方,这才有机会认识了丁惟柔。两人彼此间都有相当好感,只是丁惟柔一直认为不应该辜负朱家二少,因此迟迟不接受丁世祺。直到再次与朱二少重逢,双方正式分手后,丁惟柔才决定与丁世祺共度一生。而丁父因着丁世祺是同姓又没有显赫的家世及丰厚的家产,担心丁惟柔嫁后会吃苦,故不愿意答应这门亲 事。但丁惟柔独有主见,深知金钱与家世不可依恃。而丁世祺学养丰富,只要他们共同努力,日子再艰难也无可畏惧。于是她向父亲清楚地表达自己要嫁给丁世祺的决心。丁父最终只有接受,于是二人在1942 年步入婚姻殿堂,开启了他们人生的新篇章。
丁惟柔婚前曾与丁世祺表明她在婚后是不可能单单做一个家庭主妇,而要继续她的工作。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们一结婚就怀孕,五年连生了四个孩子,而且每次怀孕的过程都极为辛苦,甚至不能下床,工作的梦想当然也就破灭了。再加上丁先生的事业渐次开展,官场的应酬也随之增多起来。丁惟柔只好努力扮演好丁太太的角色。
抗战期间,丁世祺成为中国金融机构的一名高级主管。早在美国读书期间,他就已是“仁社”中的一员。“仁社”是由一批爱国青年留学生组成,吸引很多在学识和操守上都很杰出的青年才俊加入,目的在于彼此激励、帮助,以共同报效国家。尹仲容、严家淦、孙运璇、李国鼎等国民政府要人当时都是“仁社”的成员。身处大后方时,“仁社”成员多有联系,相互砥砺。此外,丁惟柔因着妹妹的缘故而认识了蒋经国之妻蒋方良,渐而成为好友。丁氏夫妇遂成为蒋经国容许蒋方良来往的少数家庭之一,他们亦多次与蒋经国会面。
1949年,大陆易手后,丁家迁到香港。滞港期间,长子安世不幸罹患痢疾而夭折,这件事对丁氏夫妇打击很大。时局混乱,他们决定离开官场,重回一介布衣的生活。
1950 年底,丁家移居日本,先与友人合作发展对外贸易,尔后投资经营餐馆业。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丁惟柔出任饭店经理。在她苦心经营与努力下,餐馆事业蒸蒸日上。但在此人生环境转型阶段,夫妻俩开始摩擦不断。丁惟柔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内心却非常痛苦。一直笃信个人力量的她,此时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在丁家初到日本之时,丁惟柔结识了一位陆太太,她当时珠光宝气的市侩习气给丁惟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饭店开张后不久,一个截然不同的陆太太出现在饭店,寒暄之下,丁惟柔发现她过去的许多恶习都消失了,细问之下才知道她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她找到了真正的平安与喜乐。丁惟柔心中充满狐疑,因为她过去从未见过一个人有如此大的转变。丁惟柔那时内心的煎熬使她渴求得到同样的安慰,于是在陆太太的安排之下,蔡孟坚夫人与后来在台北灵粮堂担任执事的徐刘玉棠女士前来探访丁惟柔, 并且邀请她参加周日的主日崇拜。教会中的平安与宁静吸引着丁惟柔,从此,她与孩子们就按时去教会,孩子们在主日学中获得很多乐趣,但是她自己却一直没有受洗的打算。当时香港灵粮堂的赵世光牧师常到日本讲道,在一次与丁惟柔的谈话中,使向来重视理性思考的她重新来看待信仰的本质在于信心,就在跟随赵世光牧师做决志祷告中,以前有着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气魄的她突然发现自己之渺小,第一次认知到自己的软弱。最后当赵牧师问她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生命的救主时,她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愿意。自此神彻底地改变了她的生命。1954年8月23 日,在赵世光牧师的施洗下,丁惟柔正式成为基督徒。因着领受到神无微不至的爱,她开始能够体会到自己丈夫内心的煎熬与挣扎,故在态度上有了极大的转变。由于她明显的转变,她的婆婆与孩子们相继受洗。
在个性上向来自负又极重孝道的丁世祺对基督教不拜祖先的教导极为排斥,坚决不上教会。丁惟柔心里坚信一人信主,全家都必得救,因此,她绝口不与先生辩论,私下却一直为着丈夫迫切祷告,等待上帝的作为。当时丁世祺在生意上屡遭挫折,甚至常常需要她的支持,为此他心里常常不是滋味,又急于想用工作上的成就来证明自己。1965 年,丁世祺在阿富汗开设工厂,却因厂长的疏失造成与德国合作伙伴几十万美金的损失,这对他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因此意志消沉,甚至想一死了之。但就在他远赴德国交涉的路途上,神使用一对德国老夫妇将他带到了教会,使得他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里看到了神的光,明白神能除去我们身上枷锁。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了基督信仰——神真正的响应了丁惟柔的祷告。
1961年对丁惟柔来说,是一个神带领她到另一个属灵高原的年份。那时餐馆的生意稳定兴隆,一切似乎都步入轨道。正当丁惟柔每天在餐厅事业与教会服事中忙得不可开交时,一位教会的老朋友来请她做他向银行贷款的保人。因为是多年老友,她就一口答应下来。又因餐厅太忙走不开,所以她就把图章交给老友,让他自行办理手续。想不到的是,这位友人竟然在未得丁惟柔允许下贷了五千万日币;更为令人吃惊的是,没多久那位朋友宣告破产,丁惟柔因着担保的缘故必须要偿还五千万,餐厅也就将被银行收去 抵押拍卖。消息传出,许多人都说她信教信迷了才会上这个当,这话听在丁惟柔的耳中分外刺耳。于是,她怀着一颗纠结的心向神祷告。第二天,她读到了哥林多前书6章7 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顿时她明白了神的心意,当下决定不告她的友人。由于银行也自知理亏,主动愿意降低利息让丁惟柔分期摊还。面对庞大的债务,虽然每个月丁惟柔为着摊还的金额想方设法,但她内心却很平安,因为她相信神会带领她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在外人眼里,一切如常,完全感受不到她所承受的压力。非但如此,她还尽力投身在教会服事之中;同时她调整了自己的事业,选择房屋租赁作为日后的事业重心。后来在一笔交易中,她所购得的土地竟一下子增值了四千万。丁惟柔心里清楚:除了神,没有人能够成就这事。这件事使她在信仰上从理性的选择一跃成为感性的经历,她对神的信心也愈发成长了。这也促成她日后更愿意大笔奉献,因为她深刻体认到得失之间,一切都出于神。
丁惟柔所在的东京国际教会是一所以华人为主的教会,在教会开始之际,就有许多宣教士与之配合,再加上起初的执事们多有显赫的背景,学问很好,又见过世面,经过历练,胸怀比较宽广,为人处世上又比较圆融,教会就在神的保守与众人无私的付出下开始了宣扬主道的历程。 1972年后,他们日本华人中留学生的需要,因此建立了以牧养留学生为特色的教会。因为留学生大都停留时间较短,如何提供及时而实际的关怀与扎实的教导训练,为他们打好信仰的根基,就成了教会工作的重点。丁惟柔在其中更是站在接触留日学子的第一线,积极主动的关怀远渡重洋的游子,这样的事工数十年不辍,久而久之,被人尊称为“日本留学生之母”。
由于丁惟柔积极参与教会服事,与许多宣教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之后因着这层关系使她跨入了国际事工的领域。一开始她参与日本地区的布道大会的筹备工作,负责财务;之后又陆续参与了1974 年在瑞士洛桑举行的福音大会,以及 1983 年和 1986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福音会议。基于她经营餐厅的经验,每次总是负责财务与伙食相关的工作。在与各国同工的配合中,她拓展了更为宽广的视野,也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功课。在参与这些国际性会议同时,也意外的参加了海外中国教会所推展的一项运动——全球华人福音运动(简称“华福”)。中国教会基本上倾向于各自发展,原任中国信徒布道会会长的王永信牧师有心联合全球华人教会共同推动对教会成长有益的探讨,于是借着洛桑会议的机会与与会的华人代表共同研商其可行性。经激烈的讨论与同心的祷告后,大家决定凭信心成立华人事工中心,并在1976年于香港召开了第一次全球华人事工研讨会。丁惟柔参与了该运动的创始事工,且一直担任华福的财务同工。她亦积极参加每次会议,成为华福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
丁惟柔的夫君于 1974 年9月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之后不久,丁惟柔打开自己家中的大门,使丁家成为另一个显明神荣耀的所在。当许多留日学生面对生活、学业的压力及未来的不确定性时,丁惟柔就邀请他们每周日下午到家中聚餐,一慰乡愁。两年后更开始了小组聚会的模式,除了敬拜赞美外,还邀请不同的人来分享生命的见证,从而使慕道友与初信的弟兄姊妹对基督信仰有更深的认识。若是有人遭遇任何问题,丁惟柔都能设身处地为当事人设想,引导对方面对问题,竭力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丁妈妈的家”成了一个既温暖又能增长灵性、解决困难的地方。在与年轻人接触愈来愈频繁的过程中,丁惟柔的家渐渐成为一个全天候二十四小时开放的地方。丁惟柔又是一个身教重于言教的人,她所主导的小组查经贴切于生活,又富于生命深度。丁惟柔身体力行,实际活出神的教训。信仰在她身上不是高不可攀的教义,而是蕴藏在生命中的一股真实的力量,许多人的生命也因此而改变,这正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最好见证。丁惟柔在自家所推行的事工直到她过世前从未曾间断,即使她不在日本,她也会做好安排使所有聚会能正常进行。“丁妈妈的家”永远不打烊。
丁惟柔综其一生的经验,对服事主的人有三条鼓励的建议:一是要明白“我什么都不能,但我所信的神什么都能。”凡事靠主,凡事谦卑,靠神来做神的工作。第二,我们会不断地遇到困难,但神会替你解决,要靠祷告。困难越大,祷告越迫切,万般无奈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呼求,困难都会过去。第三,不要离开神的旨意,不是出于神的事,再方便都不能做。特别是在小事上,要站在神面前,不要站在世界上边。宁可吃亏,也要站在神面前。在大事上犯错不容易,在小事上就不一定了。魔鬼的试探是从小事上开始的,先利诱,后捆绑;在小事上交托,不被利诱,在大事上就不会失脚。
丁惟柔为主尽力奔跑,直到2007年6月9日病逝于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医院,享年93岁。当时教会同工及家属围绕在病床边,由教会姜宝升牧师宣读启示录21:1-5经文,为她做最后的祈祷。她在安详中逐渐停止呼吸,回到父神的怀抱。
资料来源
- 金明玮著,《飞鹰:永远的丁妈妈》,台湾:宇宙光全人关怀,2006年。
- 基督日报,“华福运动折损大将——丁惟柔长老安息主怀”, http://www.gospelherald.com.tw/news/min_1154.htm,(2009年9月2日上网)。
- 潘刘慰慈专栏,“丁惟柔一生精彩”, http://blog.yam.com/rainbowvalley/article/1486419,(2009年9月2日上网)。
关于作者
作者王立人是美国加州美福神学院学生,在李亚丁教授指导下撰写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