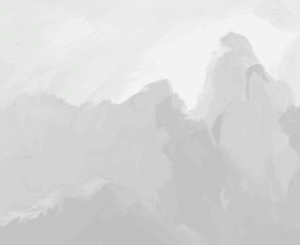1.早期生活和教育
1821年5月8日,高第丕(Tarlton Perry Crawford)出生於美國肯塔基州沃倫縣的一個基督徒家庭,其父約翰(John Crawford)是個勤勞節儉的農民,但受過教育,故也在一間浸信會教會兼職。母親盧克麗霞(Lucretia Crawford)也受過一些教育,思想開放,他們夫妻二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高第丕是他們七子三女中的第四子。
1837年,16歲的高第丕在大黑溪浸信會教會受洗歸主,從那時起,他便立志將來到海外宣教,傳揚基督的福音。19歲時,高第丕離鄉去密西西比求學,為賺取學費,他先後在許多社區、農場打工。在田納西州丹馬克男校讀書時,他在班上名列前茅。1848年初,高第丕在大哈奇(Big Hatchie)浸信會教會的資助下,進入田納西州默弗裡斯伯勒市的聯合大學學習,在讀期間,教會中許多會友在主日舉行義賣,出售自產的雞蛋和牛奶,為他籌集資金幫助支持他。1851年,年已30歲的高第丕以全班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獲得了聯合大學學位,他持之以恆,認真刻苦的精神給師生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教會和教友多年來對他的戮力支持,更堅定了他遠赴海外宣教的決心。
早在1850 年底,美南浸信會國外佈道會就已接受高第丕為傳教士,並準備把他派往中國上海宣教。在啟程赴華之前,高第丕於1851年3月在阿拉巴馬州塔斯卡盧薩縣的家裡與瑪莎·福斯特(Martha Foster)結婚。瑪莎也是浸信會信徒,畢業于阿拉巴馬州的拉斐特學院,她與高第丕同樣懷有宣教心志,可謂志同道合。
2.在上海宣教
1851年11月,高第丕作為美南浸信會傳教士,偕夫人從紐約啟程前往中國,1852年3月30日到達上海,開始了在華長達半個世紀的宣教生涯。從1852到1863年,高第丕夫婦在上海從事宣教工作。夫婦倆皆有語言天賦,到上海不過三年,他們就可以講上海方言,用上海話講道,還出版了上海方言的《讚美詩》。他們不止自己會說上海話,還用中文寫出一本教人學說上海話的書。為了幫助後來西方傳教士掌握上海方言,高第丕於1855年出版了《上海土音字寫法》。那時還沒有“上海方言”一詞,上海話被稱為“上海土音”。高第丕發明了以注音字母的方法,教人們學習上海話。這本書可以說開創了方言注音之先河,雖然最後沒有廣為流行,但卻被視為漢語拼音的先驅。此外,這本書還保留了不少當年的上海話,從中可以看到今昔上海話的變遷,為研究上海方言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1861年,由於美國內戰,造成港口封鎖,交通不便,資金短缺,美國南浸信會總部中斷了對海外宣教的經費供應,以至於海外傳教士們不得不自己養活自己。高第丕在上海只好靠教授英語課和從事些房地產生意以謀生,竟至得到一筆不菲的收入。
3.在登州宣教
1863年,高第丕夫婦因長期不習慣上海的氣候而身體大受虧損,不得不於1863年8月離開工作了11年的上海,前往山東登州(今蓬萊)繼續宣教。當時美南浸信會傳教士海雅西(Jesse Boardman Hartwell)已在登州開闢教會二年之久。1864年,海雅西也因資金短缺到上海租界工部局作譯員,登州浸信會教會就暫時由高第丕負責。1865年,海雅西在上海得到一位美國醫生朋友的私人捐助後,返回登州重新主持教會工作,高第丕就成了他的助手。後因傳教策略等方面的問題,兩人之間產生了分歧與矛盾。為實現自己的理想,1866年,高第丕從海雅西家裡搬了出來,通過漢語教師趙鼎清在登州畫河邊租賃了一處擁有7個院落,共計34間的大房子。院中有多處門廊、庭院,還有一口水井和多種樹木,頗有氣派。高第丕在這裡建立了與海雅西“北街教會”相對的、名為“牌坊街浸信會教會”(The Monument Street Baptist Church)。
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牌坊街浸信會,高第丕還計劃建造一座更為氣派的西式教堂。1871年,在美國差會本部未能及時寄來款項的情況下,他自己投資3000元,在戚家牌坊對面不遠處建起了一座西洋風格的浸信會教堂。教堂於1872年正式建成,稱為“登州聖會堂”(The Monument Street Church)。該教堂建築由禮拜堂和鐘樓聯體構成,東部禮拜堂為單層結構,內設280個供做禮拜者就坐的座位;西部鐘樓為三層,頂樓木梁上懸有做禮拜用的銅鐘,每值禮拜日,鐘聲響徹全城。這座聖會堂至今猶在,即今日蓬萊畫河基督教堂,該堂可說是高第丕在登州宣教事業的一個歷史見證。
1871年,海雅西第一任妻子因難產而去世後,帶著四個孩子返回美國。雖然第二年他又返回登州,但很快即遷居煙臺。1875年他辭職再次返回美國,從此直到1893年,登州浸信會教會一直由高第丕負責。
高夫人瑪莎與高第丕在宣教方針政策上並不都一致,她在上海時即創辦過一所女子小學堂,隨高第丕到登州後,由於有語言基礎,以及美國北長老會辦學的先例,她不久即開辦了一所寄宿男校,後來又開辦了女校,一度非常成功。但到了1870年代,由於丈夫不支持,甚至制定政策加以限制,使得學校難以維持,苦撐到1884年,為了緩和與丈夫的關係,只好同意關閉了學校。此後,她即穿上中國人的服裝,走村串戶訪問婦女,與登州城裡和周圍鄉村很多人建立了友誼,在傳教士和當地人中間享有很高聲譽。享譽世界的美南浸信會女傳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曾如此評價她說:“幾乎沒有傳教士贏得像高第丕夫人所贏得的當地基督徒那樣的尊敬。……如果我們主的愛在任何人的心中和生活中復活,那個人必定是高第丕夫人。高第丕夫人在她居住登州30年的時間裡,挨家挨戶地走訪居民,教導來訪的人,為學校學生上課,勸導婦女做公益事務,每年春季和秋季到鄉村旅行。1875年,高第丕夫人走訪了131個村莊,由此可以看出她是一個一刻不停工作的人。那時,她負責照顧一所寄宿男校的孩子們。各種各樣的責任都落在一位傳教士妻子的肩上,顯示了她對這些工作的熱愛、耐心和忠誠。”
高第丕的宣教理念和策略與美南浸信會總部,與一般南浸會傳教士很不相合,而且他的固執、不易變通的性格也引起很多人的反對。高第丕認為本地教會的費用不應該從宣教經費中支出,應當本地籌集,本地使用。早在上海期間,高第丕就決定要任用不帶薪的助手,除了他的個人教師外,他一直堅持這一原則。他始終堅持實行不用外國的錢雇傭當地助手的政策,一直認為外國基督教差會在中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實用的、注重靈性的基督教徒隊伍,在適當的時候有他們自己的牧師,發展自己的學校和基督教機構。在高第丕看來,花錢雇用中國人傳教,會導致一些信仰不純、思想不端的人為了金錢而加入教會,致使宣教體系腐化墮落。
高第丕始終堅持認為傳福音是傳教士的唯一職責。因此,他既不支持花錢辦學,也反對花錢辦醫療事業,並因此與妻子不和,迫使妻子放棄醫務工作,最後於1884年,徹底關閉了浸信會在登州先後辛苦創辦的三處男、女學校。登州浸信會在高第丕負責期間,僅在初期有過似乎不錯的發展趨勢,而進入1870年代即矛盾重重,最終他不但和同工之間不能合作,也使一些會眾離開教會,甚至高第丕夫妻之間也因理念不和,一度形同陌路。在諸事不順的境況下,高第丕陷入了對未來的深深憂慮,以致在1870年代後期,他的精神和身體都出了問題。然而,現實並沒有改變高第丕,他在自己堅持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他繼續批評美南浸信會海外宣教委員會,認為他們對海外宣教工場上的宣教事務不該有發言權,以至於南浸會不得不中止與他的關係,於1892年將他撤職,此舉迫使高第丕從此走上了不歸路。
瑪莎雖然不同意丈夫的某些觀點,但她仍然忠於丈夫。1894年,當美國南部浸信會總部派海雅西再回登州主持浸信會時,高第丕攜妻子及鮑志培(G. P. Bostick)等十數名追隨者西遷泰安另起爐灶,創建了脫離浸信會的福音宣教團(Gospel Mission)。期間一些認同他理念的宣教士陸續加入他的團隊,其中有海林(D. W. Herring)、白泰理(T. L. Blalock)、金(W. D. King)和奈特(F. Knight)女士等傳教士。有記載說,他們帶走了華北浸信會一半多工作人員。美國浸信會海外宣教部曾經試圖作出讓步,但遭到了高第丕的拒絕。
所有的福音宣教團傳教士都穿著中國服裝,深入到中國人家庭中,直接向民眾傳福音,這與戴德生中國內地的做法很相似。他們的宣教卓有成效,得到當地百姓的信賴,到世紀之交時,福音傳教團在山東已經發展到19個分會。
4.文字上的成果與貢獻
高第丕夫婦在華半個世紀,除了宣教工作外,還專心研究漢語,成果顯著,客觀上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他們二人不僅能說中文,能說上海話和山東話,還用中文出版過不少福音書冊和其他書籍。除了《上海土音字寫法》外,1869年,高第丕還與國人張儒珍合著出版了《文學書官話》(Mandarin Grammar),用漢語官話口語寫作,並把官話口語作為研究對象。全書21章,主要是用英文文法來分析中文口語文法,以便於外國人學習中文。這是最早研究北方口語語法的書,對漢語的近代化轉化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廈門大學中文系主任李無未認為該書“在漢語語法學史上發揮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並且認為日本研究現代漢語語法的重要書籍《支那文典》就是以《文學書官話》為藍本的。
高第丕還著有《族長時代》(The Patriarchal Dynasties)一書,闡述他的神學思想。
高第丕夫人也是一個多產作家,在繁重的教學、醫療和佈道工作之餘,她勤於寫作。除了平時經常寫信彙報工作、幫助丈夫闡釋宣教政策和方針外,在1877年舉行的第一次宣教大會上,她撰寫了 “為婦女開展婦女工作”專題文章,強調傳教士的妻子們要挨家挨戶走訪,親自指導當地婦女,並為她們準備合適的文學作品。在同一時期,她還編寫了《登州最初十三年宣教史》(History of Mission in Tengchow for the First Thirteen Years)。
在1880年代,出於宣教的需要,高夫人仿照西方主日學校“三隻小豬”的故事,編寫了一本兒童讀物《三個閨女》(The Three Maidens),生動地顯明信仰基督教和不信仰基督教的區別,引導人們皈信基督。這本書後來在中國各地教會廣為流傳。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到登州之後不久,她便用中文編纂了可說是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西餐種類和製作方法的著作——《造洋飯書》(Foreign Cookery),1866年由上海美華書館正式出版。該書開篇詳述了廚房衛生知識,隨後分類介紹了十七大類、260餘種西餐的用料和製作方法。高夫人纂寫此書的原本動機,乃是為著教導不懂英文的傭人為其烹調食物,不料此書出版後,卻使那些不諳英語卻又希望一窺外國飲食文化的中國民眾,成為此書的主要讀者群,令作者始料不及。《造洋飯書》出版後成為熱銷,在民國時期曾多次再版。1986年,中國商業出版社又出版了本書的校注本,可見此書在中西飲食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5.晚年歲月
1900年,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爆發,在中國宣教、生活了50年的高第丕夫婦不得不離華,回到美國。同年10月1日,他們從上海出發,於28日抵達舊金山,受到親友們的熱情接待。由於他們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中國生活,所以在美國他們沒有自己的家,在美期間,他們都是住在瑪莎的親戚家裡。大約有一年半時間,他們都在美國南部各地巡迴演講,講述在中國的宣教經歷以及中國宣教工場的需要。1902年4月,高第丕因肺炎在阿拉巴馬州妻子故鄉的親戚家裡去世,享年81歲。
高第丕夫人在中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上海11年,登州31年,泰安14年,中間只有兩次休假),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獻給了中國人民,她不僅把基督福音帶給當地百姓,也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在登州期間,她不僅創辦並堅持開辦了近20年的男生寄宿學校,培養了一批掌握一定現代知識的人才,還堅持行醫10餘年,“每年治療病人不少於1500或2000人次”。高夫人早已習慣了山東的氣候、人情、飲食、風俗和習慣,也穿慣了中式服裝,她完全把自己當成了山東人,與當地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在丈夫病故後第二年,她就回到了山東泰安,繼續在福音教會事奉。
高第丕夫婦一生沒有生育兒女,在1870年代,他們曾在日本領養了兩個英國孤兒,但從現已掌握的資料看,長大後並沒有和他們在一起生活。高夫人晚年孤身在泰安宣教,直到1909年死於泰安。
1909年,Rev. L. S. Foster撰寫的《在華五十年——高第丕傳》(Fifty Years in China: An Eventful Memoir of Tarleton Perry Crawford, D. D.)出版發行,生動、翔實地記述了高第丕夫婦奉獻、傳奇的一生。
資料來源
- Rev. L. S. Foster, Fifty Years in China: An Eventful Memoir of Tarleton Perry Crawford, D. D., Nashville: Bayless-Pullen Company,1909.
- 尋訪傳教士的足跡工作室,“精通中文與上海話的傳教士:高第丕”。2023/01/13.
- “美國傳教士在登州(系列之三)——高第丕夫婦與登州聖會堂”。 《福音時報》,2016/10/25。
- 李海英,“近代美國來華傳教士高第丕與早期白話文研究——以《文學書官話》為例”。《菏澤學院學報》,2012(3):110-114。
- ShareAmerica,“在華半個世紀、精通中文與上海話的宣教士高第丕”。2010/12/22。
關於作者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